今年1月20日,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个10岁女孩Antonella因为使用TikTok录制“窒息挑战”视频,不幸导致意外死亡。当时本来就正值数据隐私监管机构根据欧盟《通用资料保护规范》(GPDR)对这家社交网络公司调查之际,这一悲剧更使欧洲舆论为之哗然。
事后,TikTok要求1250万意大利用户确认年龄,删除50万个违规账户,并保证一旦发现13岁以下儿童开设账户,将会在48小时内删除。受此影响,儿童权益正日益引起世人关注。今年一季度TikTok移除的视频内容中,儿童安全的占比高达36.8%,远高于位居第二的“非法活动和受管制物品”(21.1%)。
这一波全球性反馈并不仅限于欧洲,自2017年以来,短视频社交网络、直播打赏等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中国也不断引发争议。截至2020年末,短视频对中国儿童的渗透率已达49.7%,并有在3年内赶超网络游戏的趋势。有人揶揄:“如果说游戏是鸦片,那短视频就是海洛因。”
社会舆论的批评主要指向抖音、快手等平台,谴责它们诱发沉溺。而不久前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版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在强化相关网络平台责任的同时,规定家庭和学校也须积极履行监护之责。
应当如何认识这一场危机?各方又应如何界定责任并行动起来?这其实远不仅仅牵涉到一个行业、一种媒体,还深刻地动摇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核心理念,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的困境如此棘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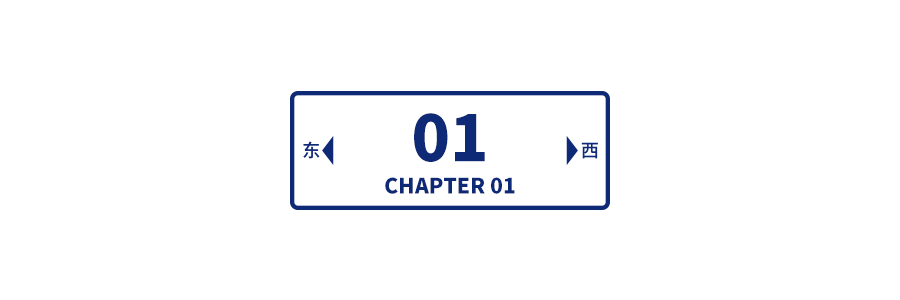
消逝的童年
当下这场危机的核心是儿童权益,换言之,人们普遍认为,童年是一个与成年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,孩子也尚未能完全履行自身的权利义务,须受到特殊保护。尽管对这一阶段的界定或许不同(如中国的“未成年人”是18周岁以下,欧盟则只严格限制13周岁以下孩子,14-18岁已被视为可为自己行为负责),但相关监管的逻辑出发点都是一致的。
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·阿利埃斯在其名著《儿童的世纪》中提出,童年其实是一种很新的现代理念——在17世纪之前古代人并不会把孩子与成人区别对待,那时童工在西欧是普遍现象,也没人觉得儿童需要得到社会照料。
在他这一论断的基础上,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·波兹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:我们现在对“童年”的特定理解,其实是印刷文明的产物,报刊书籍等印刷品的媒介特性将成人和童年区隔为两个不同阶段,但到广播、电视等电波媒体兴起之后,任何人不需要发展出阅读能力就能接触,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再度变得模糊。他断言,随着现在的孩子可以从电视上接触到与大人没什么两样的丰富信息,他们的心理变得更为早熟,更快丧失纯洁的童心,导致儿童独特性正逐渐丧失。
他这本书出版于1982年,主旨是批判美国盛行的电视文化,忧心电视对家庭的入侵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。但可想而知,相比起电视,如今的视频社交网络所带来的冲击甚至更为深远——想想看,只要你能上网,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,成人和儿童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在技术上没什么两样,“童年的消逝”很可能正在加速。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那个10岁意大利女孩的悲剧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模仿成年人的结果。在她去世后,其父说:“她想成为女王,成为TikTok的明星,她成功了。“在她的生活里,TikTok和YouTube就是全部,她小小年纪就渴望获得所有人的关注、点赞、认同。
多年前,意大利作家翁贝托·埃科就注意到,当代社会已经成了一个“所有人都在持续大幅度流动的社会”,家乡和根的概念将被彻底淡化,孤立的个体缺乏与他人的有机交往,“他人”已经成为相距遥远、仅仅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的群体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为了不坠入默默无闻的黑洞和被人淡忘的漩涡,人们不惜一切代价,拼命展示自己”,想要享受成为他人关注、议论对象的那种美妙感觉。
只不过,在以往的年代里,一个普通人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,更别提一个孩子了,毕竟“在电视上露脸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,但如今视频网络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上“三分钟的名人”。这既激发了无数人的梦想,又让还不知道如何驾驭它的孩子遭遇了意外的悲剧。
明白了这些,就能让我们看到:在网络这种全新的传播技术之下,视频社交媒体并不仅仅只是给人带来一些“有趣、可分享的内容”,它实际上对全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冲击。借用传播学权威哈罗德·伊尼斯的话说,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都会产生三种结果:改变人们的兴趣结构(人们所考虑的事)、符号的特征(人用以思考的工具),以及社区的本质(观念起源的地方)。不难想见,儿童又是应对这一冲击最脆弱的群体,因而引发的争议也最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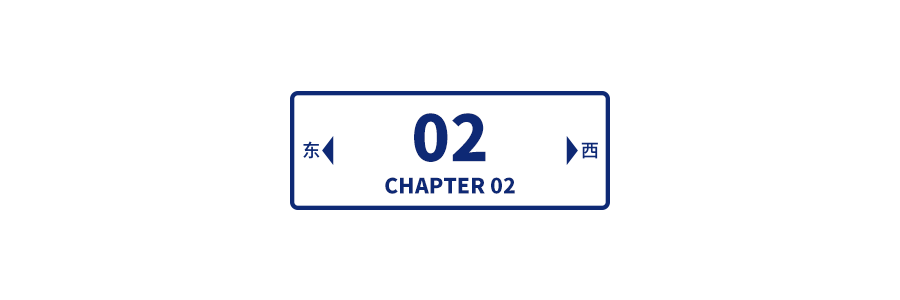
怎样才能救孩子?
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,相反,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是:技术总是走在道德伦理前面,以至于当一种新技术带来冲击时,人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新理念去应对它,而此时也最容易引发各方争论,因为谁都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恰当合理的。
不管怎样,我们至少有一个共识:必须“救救孩子”。尽管多少年来,“童年”在电视、网络的冲击下正在“消逝”,但看起来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儿童不应受到特殊对待,问题只是在新的情况面前,如何保护儿童权益。
客观地说,对新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冲击,许多网络平台自身也始料未及,这都是需要在不断摸索中刷新认知的,因为没有一种新技术能在问世之初就充分预见到所有后果——就像互联网最初也只是为了在军事连接,谁也想不到最后竟在社会、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。这既不是说出了问题就一刀切(饱受批判的电视也没关掉),更不是说什么也不做,而是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。
技术层面的措施可以不断优化改进,难的是如何有针对性地界定、探讨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当下的全球性反馈中,不同社会的着眼点是有些微妙差异的。乍看似乎都是平台监管的问题,但今年2月欧洲消费者组织在欧盟委员会申诉时,重点是“TikTok违反了多项欧盟消费者权利,未能使儿童免受隐藏广告和不适内容的侵害”;而中国社会则更多地聚焦于成瘾、打赏。
换句话说,欧洲人注重的是保护儿童作为消费者的特定权利,但中国人则更多的是从家长的立场出发,真正担忧的是孩子耽误学业,又或乱花家里的钱带来经济损失,在意的其实是由此引发的社会危害性。

黑龙江初中生钟美美,在短视频平台模仿老师而走红
事实上,中国社会对视频社交的批评,并不是担忧它的机制让孩子自发“拼命展现自己”(钟美美模仿老师爆红后,普遍肯定他是“鬼才”),更多的是强调孩子沉迷于追星,为此浪费了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
面对当下这个全新的挑战,我们实际上需要一种新的伦理规则,能使我们兼得新媒体带来的好处,又不至于伤害孩子。棘手的是,不仅儿童和成人的边界本身是模糊的,而且孩子之所以会沉迷于短视频,并不仅仅是被内容所吸引,还因为内在深层次的社交需要——他们渴望与人分享交流、被人关注,渴望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享受成为英雄和女王的感觉,毕竟现代社会到处都在说“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成真了呢”。
毫无疑问,现在的监管模式还可以再优化,但这说到底是“堵”而非“疏”,如果不能回到根本上,解决孩子“为什么沉迷”的问题,这最终仍会事倍功半。很多社会调查都一再证明,一个沉迷的孩子,其实往往是因为家长在其成长中缺乏情感支撑,没能给到孩子足够的精神滋养。生活越是单调乏味,兴趣就越窄,也越是会沉迷于虚拟世界。孩子的成长,靠盯是盯不住的,与其寄望于平台的自律,不如从小培养孩子本身的自律。
让孩子完全隔绝于网络不现实也没必要,真正应该做的,是让新媒体扮演一个更为谦卑的角色,回到“科技以人为本”,提供对孩子益智、有用的内容,但我们需要想清楚的是:当下视频社交媒体的危机并不只是“一个问题”,而是一堆问题的症结,因而只有各方都行动起来,平台自律加上家长正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,它能有望解决。

 手机扫码打开
手机扫码打开
